网络借贷领域的问题失败了,然后呢?
众所周知,传统金融法律治理的有效方式是对涉众、公开和不特定人的行为进行禁止并辅以刑法制裁。互联网金融时代的最大特点是公开、涉众、与不特定人发生交易,但如果理念、制度和治理监管不适应,极易造成群体性的社会稳定问题。金融科技化、网络化和数字化的背景下,应该摆脱对公开、涉众、不特定人这种刑事治理逻辑的恐惧,进而向小额、分散、特定化、适当性、信用、安全转化,促进互联网金融良性要素的有效发挥。以往互联网金融尤其网络借贷领域的失败问题根本上说是缺乏有效法律制度的失败。
互联网金融法律制度存在空白
我们需要厘清互联网金融立法的演进基础。互联网金融技术的应用本应涉及到货币支付、网络借贷、股权众筹、信托理财、资金保险等领域,但由于对公开涉众形态的恐惧,加之缺乏法律针对涉众型的互联网金融的明确科学规范,实际应用的发展十分缓慢。我国目前在互联网金融领域法律制度上基本空白,已有的以禁止为主。例如,货币领域以禁止为主、股权众筹领域以禁止为主、信托理财领域以禁止为主。互联网商务信用与金融信用存在边界不清。以蚂蚁芝麻分为例,由于涉及到信用,芝麻分不能叫做芝麻信用分而仅能称为芝麻分。而法律制度的不良领域,则以网贷为典型,有关部门出台的调整网络借贷的制度,制度执行效果极差,与现实生活完全背离,属于不良法律。

法律制度的空白或不良造成了刑事过度的后果,例如比特币击穿货币约束制度,外汇、洗钱、行贿受贿难以处理;P2P网络借贷机构出现挤兑倒闭,投资者集体维权、上访、闹事等情况;数以万计的网络借贷纠纷案件法院不予受理,互联网法院不受理P2P网络借贷案件;而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最终只能以刑事兜底。互联网金融风险整治事实上成了公安机关的派出所、社区街道为一线的强行关门行动,从事互联网金融行业的企业或负责人成为“限制出境”等措施的“类涉嫌犯罪”对象,合法经营的互联网借贷企业缺乏制度预期等,社会反映强烈。
打破互联网金融法律设计误区
互联网金融是科技金融,能否有效发挥利用取决于制度设计,取决于创新与风险约束的平衡制度。未来互联网金融法律的设计应该打破以下误区:
第一,公开、涉众、回报就是风险。公开、涉众、人数众多的涉及金融的确存在风险的可能性,但如果配套制度适当,就可以有效控制风险。现今金融科技使普惠金融成为可能,利用技术控制可以实现小散微的定位。如美国的股权众筹制度中,人数不限但对投资者采用12个月内网络投资不超过2000美元的限制(个别特别富有的人最高不超过10万美元)。

第二,信息中介、不得增信、打破刚兑就可以消除风险、保护投资者。这一认识存在事实上的逻辑错误。信息中介注定无法保护投资者,作为网络借贷的中介平台,承担着合格投资者和借款人的审核、信息披露、信用评估、风险控制、技术信息安全等职责,只有针对互联网金融的特点规律赋予网络借贷机构权利并承担义务,有担当的平台才有能力保护投资者(出借人)。P2P网络借贷最大失误是不顾新金融实际玩概念,凭想象,不顾我国信用信息现实的理想主义。我们主张借鉴英国的复合中介、可增信、可转让和可垫付,承接众多出资人诉讼资格而代为行权机制。当前,互联网法院不受理P2P网络借贷案件,值得反思。

第三,牌照制就可以消除或管制风险。牌照制、备案制都是解决主体合法性程序问题,可以分清合法经营与非法经营的边界,但牌照制没有防范风险的特别作用。事实上,合法的企业主体风险兜底或发起人、实际控制人对网络借贷机构风险兜底才是基础。
第四,司法裁判规则就是行政监管规则。法院审理的案件归根结底是一种纠纷,原告希望通过公权力强行保护自己的权利,因此,法院需要平衡可保护的力度和强度。而行政管理则直接是为了维持一种可容忍的市场秩序。由此可见,当前有关部门不制定利率标准,而是将司法裁判规则作为标准利率,这是存在明显逻辑错误的。互联网金融治理的基本逻辑应该是:首先由市场主体自由运作,行政监管跟上,最后再由刑法对越位或不良行为予以刑事打击。

第五,刑事手段可以保护网络借贷投资者权益。网络借贷机构是信息中介,出借人与借款人的关系是民事关系,除非网络借贷机构与借款人串通诈骗或平台虚假标自融犯罪,清晰的民事法律关系应诉于民事解决。但是众多出借人主张权利困难、民刑交叉不清、网络借贷法律地位不清晰,导致刑事手段处理往往被优先考虑。然而,由于刑事手段的责任是打击犯罪,其注定不是保护出借人利益的有效选择,一旦动用刑事措施,受《刑事诉讼法》等程序约束,由于几年难结案,财产处于冻结或贬值状态,好资产当成垃圾处理,结果只会使受偿减少。民事问题民事解决才是更好的解决之道。
互联网金融立法把握尺度不越界
我们展望一下互联网金融法律演进的未来。
第一,充分立法。要认识到互联网立法刚刚起步,互联网金融领域面临着高规格法律的缺失、空白问题,这是我国大量、充分立法的前提。第二,分离立法。立法过程中一定要将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立法分开。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分属完全不同的两个体系,想要揉和立法、统一调整,亦或以一句“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批准,不得从事……”了事,是不可能的。特别是在地方金融层面,其“7+4+x”的架构随着民间金融的扩展而不断扩展,这就注定了民间金融需要立法保障。借助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开展的民间借贷网络化,是传统民间借贷的新形态,不能以正规的银行金融思路简单化处理,如果承认民间借贷属于民间金融属性,需要按照民间融资的制度设计规范,同时赋予地方政府以管理权力。

第三,精准立法。围绕合规与审慎经营,以及风险责任归于企业防控的理念,有什么问题用什么制度解决。解决好平台经营能力和防流动性风险能力问题;解决平台复合中介、信用数据对接、评估、增信和利率控制、债权转让、债权权益转让许可经营问题;解决借款人虚假欺诈问题,以及共债、失信制裁等问题;解决网络借贷中介机构弱势群体问题,增强对其保护(身份合法化)、赋能、权利义务对等;解决投资者(出借人)适当性问题;解决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要求,加大信披违法责任;解决平台数据安全和宣传问题。
第四,解决好利息与中介费用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中,一定要避免利息与中介费混淆的情况。例如,借款利息网络借贷诉讼中,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支付的利息、逾期利息、违约金等超过民间借贷利率保护标准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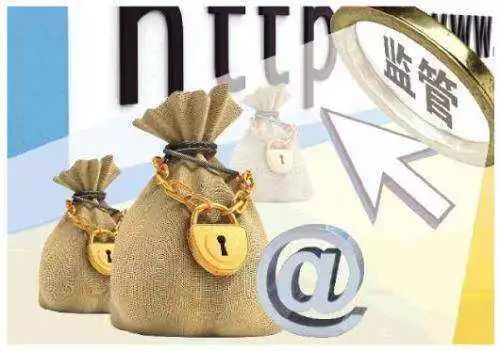
第五,行政处置的前置性立法抑制刑事便利化。互联网金融需要行政处罚的前置性,这有利于精准打击犯罪、避免过累,同时也顺应了投资领域最终实现责任自负的趋势。
总体来讲,互联网金融演化的立法会越来越多,形势会越来越好,但最希望看到的是民行刑把握尺度、均不越界即好。
责任编辑:何周重







